男女主角分别是抖音热门的其他类型小说《一位东北出马仙的孙子回忆录全文》,由网络作家“烧烤配红酒”所著,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,本站纯净无弹窗,精彩内容欢迎阅读!小说详情介绍:仙坛早收了。”可那女人一句话,把她心敲动了:“你也有孙子的,你看着小五,要是他出了事,你咋整?”奶奶沉默了很久,最后叹了口气,说:“你家这事儿,是横事,我不敢看太细。但我试试,让他们指个路。”她让人点了三柱香,在供桌前铺了一张旧黄布,把香灰撒在黄纸上,又拿出一面铜镜,面对香火晃了晃,然后闭眼开始念。屋里一瞬间静得可怕。香烧得很快,火头蹿得高,铜镜上映出模糊的影子。我趴在门口看着,看到奶奶额头渗出汗来,脸色越来越白,嘴里开始说些我听不懂的词。忽然,她睁开眼,对那女人说:“你家那孩子,在东边。地不高,有水,旁边有棵断了的树。”那女人听完愣住了,一边道谢,一边飞奔出门。三天后,那孩子果然被找到,在邻县的一处荒地边,被人绑着扔进排水沟旁的棚...
《一位东北出马仙的孙子回忆录全文》精彩片段
仙坛早收了。”
可那女人一句话,把她心敲动了:“你也有孙子的,你看着小五,要是他出了事,你咋整?”
奶奶沉默了很久,最后叹了口气,说:“你家这事儿,是横事,我不敢看太细。
但我试试,让他们指个路。”
她让人点了三柱香,在供桌前铺了一张旧黄布,把香灰撒在黄纸上,又拿出一面铜镜,面对香火晃了晃,然后闭眼开始念。
屋里一瞬间静得可怕。
香烧得很快,火头蹿得高,铜镜上映出模糊的影子。
我趴在门口看着,看到奶奶额头渗出汗来,脸色越来越白,嘴里开始说些我听不懂的词。
忽然,她睁开眼,对那女人说:“你家那孩子,在东边。
地不高,有水,旁边有棵断了的树。”
那女人听完愣住了,一边道谢,一边飞奔出门。
三天后,那孩子果然被找到,在邻县的一处荒地边,被人绑着扔进排水沟旁的棚子里——人没死,但伤得不轻。
据说那棚子旁正好有棵劈了一半的槐树。
李家人提了大包小包来送礼,被奶奶一把推了回去,说:“仙家出力,不收重礼。”
可那之后,奶奶病了一场。
整整躺了七天,吃不下东西,连话都不愿说。
我爸说她这是“压了阳火”,人还活着,魂走了一截。
我那时守在她床边,看着她苍老干瘦的脸,第一次意识到:她不是神,她只是个老太太,只是那个为了别人把自己掏空了一辈子的奶奶。
她醒来的那天,望着屋顶,声音很轻:“以后别再求我了,我真动不了了。”
她说完那句话,就再也没“看过事”。
但我知道,她心里,从来没真收坛。
因为香台还在,黄符还挂着,堂屋永远留着那一盏红灯笼,一年四季,灯不灭,香不绝。
奶奶走的那年冬天格外冷,雪一夜落到半人深。
她早就知道自己快不行了。
那年腊月,她把香炉洗得干干净净,把符纸一张张叠好封进木匣子里,还特意让爸把老堂屋的窗户刷了一遍新油漆。
她说:“我走了以后,这屋也该歇歇了。”
她不肯进医院,只说:“我这身子不是病,是散了。
接了一辈子,缘尽了,该还的时候就得还。”
那天夜里,我守在她炕边。
她声音已经很弱,却还是一口气跟我说了很多话。
她说她年轻的时候根
之间的气场错没错。
你看得出来,就能挡一劫。”
那一晚我做梦,梦见堂屋里坐了很多人,他们不说话,就盯着我笑,我吓醒的时候,枕头下多了一截烧过一半的香。
我不敢问是谁放的,也没跟任何人说。
我只是知道,从那以后,我再没敢往奶奶屋里多看一眼。
我从没见过奶奶“上仙”的样子,只听说过一次。
那年我六岁,正值三伏天,天闷得像要把人熏化。
邻村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突然“疯了”,光脚在田里跑,嘴里一直念:“别缠我,别缠我,我不欠你们的……”送去医院,说是急性精神病,打了镇静针也没用。
后来她婆婆托人找到奶奶,说她媳妇其实不是疯,是“落了仙”。
奶奶听了那人的话后,沉默了半晌,只说了句:“她不是落仙,是前缘未断。”
当天晚上,奶奶换上那身黄底红边的仙衣,在堂屋设香台、摆供果、画镇纸,亲手在供桌前画了一道“请坛符”。
我趴在堂屋外的窗台上偷偷看着。
她将供桌两边各放了一碗水、一盏油灯、一根拂尘,香插了九炷,绕成圈点燃。
空气里立刻飘起一股说不清的味儿——像烧狐皮,又像老烟锅。
奶奶坐在供桌前,闭眼不语,双手合十。
开始只是沉默,后来嘴里开始嘟囔,语速越来越快。
突然,她猛地抬头,一口气吹灭了油灯。
那一刻我看见她的眼神,完全变了。
像不是她自己了。
她站起来,走到门口,对那个女人说:“你欠她的,是你娘胎里说的那句话。”
女人原本疯疯癫癫地挣扎着,突然定住了,瞪大眼睛: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?”
奶奶没答,只说:“你梦里老出现那双红鞋,是你姐姐的。
她小时候淹死的时候,你躲在河边不敢喊,你妈不知道。”
女人突然就哭了,跪在地上,不停磕头,磕得地板都红了。
我当时吓坏了,眼睛睁得发酸,手心出了一层汗。
我不知道奶奶是怎么知道这些的,但我知道,这事是真的。
后来我才知道,那天晚上是奶奶第一次“正式接坛”,也就是“出马”。
有人说她本来命不带仙,是硬给请下来的;也有人说她小时候大病一场,梦里跟狐狸说过愿,那仙就记下了。
我只记得,她第二天整整睡了一天一夜,醒
前几天,他还是会自己早起,把堂屋擦得干干净净,在香台前插上三炷清香,嘴里不说什么,只念一声:“妈,回来歇歇。”
而我,不知为什么,从奶奶走后,每年清明那晚都会做同一个梦。
梦里我站在奶奶堂屋门口,灯笼亮着,香台冒着烟,屋里还是她坐在炕头,穿着那身旧黄绣衣,拂尘放在手边,旁边坐着几个模糊的人影。
他们不说话,只默默点头,看着我。
奶奶看起来比以前更年轻一点,眉眼还是温温的,她对我笑,说:“小五,长大了。”
我在梦里问她:“您现在在哪儿呢?”
她说:“我不在他们那儿,我还在这屋里坐着呢。
咱家香没断,我走不了太远。”
她说完这句话,梦就散了。
有一年我跟老婆回村扫墓,整理屋子的时候,我翻出奶奶用旧布包起来的香炉。
炉底夹着一张折好的黄纸,我小心拆开,上面写着一行熟悉的字:“仙不进门,人不请神。
你若不接,我便不留。”
那一刻我站在原地,许久没动。
我知道,我这一生可能不会接仙、不会“看事”、也不会再请坛搭供。
但奶奶守了一辈子的那个规矩,我会记得。
所以现在每年清明,我也会点三炷香,不拜谁,只站着,等香烧到一半,轻声说一句:“奶,我还记得。”
有时候香会往右歪,有时候香火会蹿得高一点。
有人说是风,我不解释。
我知道,那是她回来了。
她回来看看我们,看看这屋子,看看——她一生守着、从不喊苦的这间香堂。
来后喝了一碗凉开水,脸色苍白,却一句话也没提昨晚的事。
我问她:“奶,你怎么知道那女人的事?”
她没看我,只是把拂尘挂回墙上,说:“不是我知道,是他们告诉我的。”
我不敢再问。
只是从那以后,奶奶屋的香,就再也没断过。
有一年夏天,那是我第一次,亲眼看到奶奶“看事”的全过程。
那天中午,天热得要命,村口晒谷场上都没人影。
家里也没点火做饭,奶奶只泡了一碗凉白开,坐在堂屋烧香。
我正躺在炕上犯困,院门“咣”一声被推开了。
是王二叔,邻村的。
他一进门就跪下了,抱着奶奶的腿哭,说:“婶儿,你救救我闺女吧,真不能再拖了……”<我妈赶紧拉我去屋里,不让我看,但我没听话,偷偷跑去东屋窗台下趴着,透过窗缝看进去。
奶奶没骂王二叔,扶他起来,只说:“这事儿我梦见了,昨晚就该来找我了。”
原来他家闺女,才九岁,突然每天晚上发烧、说胡话,说屋里有个老太太坐炕头看她睡觉。
村里人说是吓着了,也有人说那孩子“招脏了”。
请了两拨外地先生都看不了,说她魂不齐,得送魂。
奶奶让王二叔把孩子带来。
小姑娘瘦瘦小小,脸煞白,眼神却不飘,看人直直的。
奶奶没直接看她,而是先把香台点上,拿来三根刚烫过的细黄绳,分别绕了女孩的头、腰、脚一圈,然后泡鸡蛋。
鸡蛋清倒进碗里时,奶奶皱了眉。
蛋清里,清楚地浮出一张脸,不男不女,嘴角歪着,像在笑,又像在咧嘴哭。
奶奶点了三柱香,对王二叔说:“你家老屋是不是前两个月挪了神位?”
王二叔一愣:“是是,我妈去世后,我把她供的堂口收了,说家里没人看了。”
奶奶冷哼了一声:“她守你家几十年,你说收就收?
她不走,跟你闺女讲理去了。”
屋里一瞬间安静得出奇,小女孩忽然说了句:“她说她冷,没了屋。”
声音干巴巴的,像不是她自己说的。
奶奶没惊慌,只说:“那好,我替你家补个位。”
她起身,从墙上取下一张未用过的黄符,在上面画了七道符线,口中不停念咒,最后点香化了符纸,将灰倒进米水中,让小姑娘用手抹额、洗脸。
然后,她带着王二
从小我就知道,家里不止住着我们一家人。
不是因为我撞见了什么“鬼”,而是因为有些规矩,太不寻常。
我家在东北,住的是那种老式砖房,堂屋门口挂着门帘,院子里种了一棵大柳树。
爷爷去世早,我跟爸妈和奶奶一块住。
奶奶是出马仙,但没人敢明着说。
每到初一、十五,奶奶都会在堂屋里烧香,那香不是普通的香,而是她特地从“山上人”手里请的“三炷长香”,说是专供仙家的,头不能歪,香不能断,断了就得重新请神。
小时候我总觉得奇怪——为什么别家过年炸丸子,我们家却总在屋里点香,烧符,泡鸡蛋?
有一次我好奇,问奶奶:“你为什么总给神烧香?
他们吃吗?”
奶奶不回答,只是摸了摸我的头,说:“不是给他们吃,是让他们看着咱。”
那时候,我不懂什么叫“看着咱”,直到我亲眼看见,有人从镇上带着鸡蛋、黄纸、两根烧过的香上门,跪在我家院子里哭着求奶奶。
那是一家三口,女人抱着孩子,男人脸色煞白。
男人说他儿子夜里老哭,说有个红衣服姐姐要带他走。
去医院查不出病,说是“夜惊”,开了药也不管用。
奶奶先不接,摆手说:“看事不是随便的,不是钱的事,是有没有缘。”
那男人硬是在院里跪了一宿,第二天一早奶奶才答应帮忙,说:“缘,是有的。”
那天我第一次看到奶奶“看事”。
她在屋里铺了一张黄布,把鸡蛋在温水里泡了半小时,然后倒进碗里。
蛋清慢慢往四周散开,像是长出了一只狐狸头,眼神还冲着门口。
奶奶低声说:“不是病,是冲了喜。”
她又问:“你家是不是刚把灶台往北边挪了?”
男人一听脸都绿了:“是是,前两天刚换的,说那样做饭快。”
奶奶叹口气:“你家那块地原来是人埋过胎灵的,灶口一冲,东西就出来了。”
她写了张符,让他们用红绳栓着挂在厨房灶台前,又烧了一碗米水,说晚上在家门口泼一圈,别让孩子再出门。
那家人谢了又谢,走的时候连香灰都要回去,说是“带着护家”。
我那时年纪小,只记得屋里那碗蛋清越来越清亮,最后仿佛散成了一张笑脸。
后来奶奶告诉我:“真看事,不是看病,是看人和事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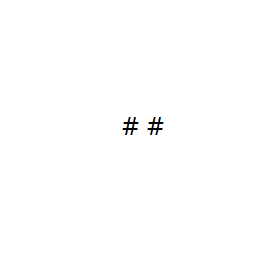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