男女主角分别是刘闪刘禅的现代都市小说《畅销巨作穿成阿斗,打造千古盛世》,由网络作家“排骨”所著,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,本站纯净无弹窗,精彩内容欢迎阅读!小说详情介绍:小说叫做《穿成阿斗,打造千古盛世》是“排骨”的小说。内容精选:竟不是历史,各位看官仅供娱乐,不必深究。......
《畅销巨作穿成阿斗,打造千古盛世》精彩片段
董允、郭攸之送来刘闪想要的资料,由于不能完全识这个时代的文字,刘闪只能让他们口述,自己重新记录了一份。看着这些材料,刘闪深切感受到大汉当前的危机和战争的残酷。
在汉代的鼎盛时期,全国人口数大约在五千万左右,据他们提供的数据,现在魏、蜀、吴三国人口总数仅有800余万!其中大汉的人口大约105万,而吴、魏两国的人口数大约在240万和450万左右。
在这个时代,战争几乎全部以人为主,人口数量是一个国家战力的重要指标,大汉竟然不到魏国的1/4,如果再这样消耗下去,最终灭亡的必是大汉!
现在的大汉,军队只有20来万,能算得上“精兵”的不足10万,这个数量与魏、吴两国的80万和40万相比,简直少得可怜。
难怪诸葛亮每次北伐都不敢涉险,如果失误一次,哪怕折损个几万兵卒,对大汉来说已是沉重的打击!然而,这对吴、魏两国来说却不值一提!
看到当前的粮食产量,刘闪又捏了一把汗!
当前,国内的军粮主要以稻谷和部分小麦为主,在蜀中各地,这些都是一年生作物;只有部分地区少量种植了一些豆类,主要用于马料。
现有的粮食生产量,只能基本满足国内百姓的温饱,就算想扩充军队也无多余的粮饷,如果再出现自然灾害或人为的战争损失,必将出现难以预料的后果。
当前的益州,除成都平原以外,很多地方都是丘陵地带,适合种植的红薯、土豆、玉米等农作物都在明朝前后才会传入,刘闪觉得特别可惜。
在刘闪生活的现代,经常有人指责诸葛亮和姜维穷兵黩武,空耗了大汉的国力,这确实有一定的道理。
按他们的说法,如果诸葛亮和姜维能让大汉休养生息,等到兵强马壮时,再与魏国决战方为上策。
以前,刘闪也是这种看法。然而,他看到这些资料之后,终于理解到诸葛亮和姜维的无奈:他们的数次北伐,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。
道理很简单:大汉在休养生息的同时,吴、魏两国也在休养生息,这两国的战争潜力是大汉的2倍和4倍!正所谓“强则恒强”,不论战或不战,大汉始终是最弱的一方!唯有设法以少胜多,以战止战,才是上上之策。
刘闪既不懂行军布阵,也不懂兵法韬略,想要以少胜多或多打胜仗,除了拥有魏延、姜维这样的良将之外,兵卒的战斗力和武器装备也是重要因素。
这个年代没有基础的科学研究,没有相关的技术人员,更没有配套的原材料生产工厂,就算刘闪拥有许多知识,他也不可能造出飞机坦克等先进武器。
刘闪只能琢磨着,能否依靠自己超越这个时代的见闻和知识,将现有的各类武器加以改进。
“陛下,你不宜再往前走了!”黄晧小心地提醒道。
刚才,刘闪心里一直在想事情,经过黄晧的提醒,刘闪这才注意到,眼前的建筑跟披香殿有点类似,应该是某个妃嫔的寝殿。
刘闪停下脚步,疑惑地问道:“为何?”
“陛下,这里是永宁殿,是张皇后的寝殿。”
刘闪想起昨日翻牌子时那位内侍的话,心里也很好奇:这位张皇后能让刘禅十年不想见她,到底得有多丑?
“无妨,朕去看看!”
刘闪径直往里走,黄晧急忙上前两步拦住,躬身说道:“陛下,要不要先去通传?”
“不必,你们不用跟来!”
“诺!”
刘闪怕被张皇后的丑陋吓跑,从而引起尴尬,于是轻放脚步,慢慢地进入殿内。
殿内被打扫得极为整洁,却十分冷清。
殿后方是小花园,一名青衣婢女,正拎着水桶浇灌园内的花草,刘闪只能看到她的背影和及腰的长发。
此女子大约二十五六岁年纪,比自己略矮一点,从背影和侧面看来,她长得比较丰满,估计120斤左右,身体十分健壮,完全不像张贵人或其他婢女那般弱不经风。
桶里的水很快就用完,女子快步走向井边,熟练地放下木桶。片刻之后,她轻松地单手拎着木桶来到园边。
这一次,刘闪看清了她的面部,这是一张娃娃脸,白晰的圆脸蛋未施粉黛,看起来肉嘟嘟的十分可爱,刘闪很想上去捏两把,最终还是忍住了。
永宁殿并不大,刘闪四周看了看,仍然没找到那位长得很丑的张皇后,也没看见其他的婢女。
刘闪知道,后宫的嫔妃由于等级的不同,配置的婢女数量也不同,披香殿的张贵人身边有四个婢女,而这里却只有一个。
婢女正在细心地拔除园内的杂草,刘闪确认永宁殿只有她一个人,寻思着,或许张皇后带着婢女,向吴太后请安去了吧。
没有见到奇丑的张皇后,刘闪难免觉得有些郁闷,悄悄地退出了永宁殿。
黄晧立刻迎上来,刘闪未等他说话,提出想参观生产和储存兵器的武库,黄晧脸上满是欣喜,几名内侍急忙离去。
少时,几名内侍眉飞色舞地拎着几个笼子过来,笼子里,竟是几只体型健壮的斗鸡!刘闪自然哭笑不得。
原来,刘禅特别喜欢斗鸡,又惧怕吴太后和诸葛丞相,经常以“巡查武库”为名,瞒着他们前往宫外斗鸡,这些事情自然瞒不住众大臣,但刘禅毕竟是皇帝,他们也不敢说什么。
前几日丞相病危,近两日又逢丞相病故,在这个特殊的时候,黄晧不敢再提“巡查武库”之事,如今刘闪主动提出,难怪他们马上就来了精神。
刘闪未动声色,询问了宫中斗鸡的数量后,立刻下令,将三十多只斗鸡,全部送到膳房做成鸡汤,黄晧纵有万般不舍却不敢违抗。
“报!”
就在刘闪即将巡查武库时,一人飞奔而来:“陛下,南人再发叛乱,越巂郡郡守被杀!”
卧槽!难道自己穿越而来,做了某些事情改变了历史?诸葛亮七擒孟获之后,南中地区便从此归顺大汉,史书上不都这么说吗??
现在北有强魏,东有吴国,南有叛乱,简直是危机四伏!
难道……自己注定是个亡国之君?
“传众臣,崇德殿议事!”
文中的人口数量借鉴晋初史料统计,作者考虑到在这之前几十年仍有战争,所以适当加了一些;此人口不含“蛮”、“羌”等“外族”;作者尽量保证数据的准确性,但本文毕竟不是历史,各位看官仅供娱乐,不必深究。
刘闪让人从医馆找来几个瓷钵和磨杵,将硫磺敲碎后放入钵中,研磨着硫磺的同时,心里恨恨地咒骂着反叛的姜维,也在咒骂着自己。
姜维反叛,确实是自己用人不当。他自己反叛倒也罢了,竟然带着巴东郡刚刚征收的粮草,还带着5000兵卒,并且吴班和高翔二将也跟着他投敌,这种事,在大汉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。
身穿凤袍的张星彩见刘闪脸色不好,一直没有插话,只是慢慢地研磨着自己钵里的硝石,几名婢女也放下其它事情,用心地研磨着许多木炭。
刘闪记得自己上高中的时候,化学老师曾提过“一硫二硝三木炭”的配方。只不过在那个时代,硫磺和木炭易得,但硝酸钾却属管制药品,普通人自然没办法去测试。
秦始皇虽然统一了度量衡,但这个时代没有精确称量物品的电子称,刘闪只能在医馆找到一把铜衡杆,可以基本准确到“钱”这个单位。
几种药品已经研磨得极细,刘闪按配方口诀将几种物品混在一起,小心地研磨混合均匀,然后把混合好的黑色粉末,均匀地撒在一块麻布上。
带着火星的干木条慢慢地靠近麻布,直到完全触到这些粉末,仍没有发生想象中的剧烈燃烧,只有星星点点的小火星,以及断断续续的噼啪声。
难道化学老师说错了?刘闪大失所望,详细排查了自己配制“黑火药”的每个过程,还是找不到试验失败的原因。
刘闪拾起一块木炭,在地上写下记忆中的那条化学反应方程式,研究了许久才恍然大悟:原来,老师教的不是这三种药品的“重量”配方!
“一硫二硝三木炭”,只是老师为了方便学生记忆,自己归纳的配平这个方程式的方法,这里的“一二三”只是不同药品的分子份数。
这会儿已经很晚了,先前研磨的三种药品不够再做一次试验,刘闪只好拉着张星彩先去就寝。
刘闪曾经说过“一有情况立刻来报”,信使自然不敢耽误,三更和五更时分,又收到两条战报。
一条是巩志所发的请求援兵的奏表:永安城已经岌岌可危,城中只有五百来个兵卒;另一条是探马报来的消息,证实姜维已经降吴,他亲自领着一千兵卒,将粮草押运至吴国巴东城,吴军主将全琮率兵与他同行。
刘闪知道,自己收到奏表时已在一天以后!在当前这时候,永安城肯定已被吴将攻破!
刘闪只能祈祷,希望廖化的兵马早日到达朐忍,否则,空虚的巴东郡定然不保。
今日,刘闪并未上朝。天已大亮时,他仍然沉浸在温柔乡里;另一方面,他是不敢面对众多大臣,正是自己的瞎指挥才让永安失陷,并且让守将巩志和李丰生死未卜。
永宁殿的婢女都是新来的,刘闪猜想她们是不是经过专业的培训,她们都会察言观色:刚刚听到房里有动静,刘闪还未开口,她们就来到榻边,侍奉自己和张星彩起身;两人刚刚洗漱完毕,桌上已经摆好热气腾腾的早膳。
刘闪昨夜并未听到声音,也不知道她们是何时研磨的药品,几个小木箱里已经装满了极细的粉末,如果只靠她们几个人,磨了这么多,应该一夜没睡。
“星彩,这点铢钱可不够赏赐啊!”刘闪呵呵笑道:“赏!每人赏一千铢!”
刘闪顾不上吃饭,重新配好一份药品,然后小心地用燃烧的木条,缓缓靠近这些黑色的粉末。
“扑哧!”
明显的火焰腾起一米多高,殿外顿时被一团黑烟笼罩,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硫磺香味。
试验的时候刘闪知道危险,虽然离得较远,手上和脸上仍被熏得焦黑,张星彩和十几名婢女吓得大惊失色。
“陛下!”
黄晧倒是勇敢,不顾一切地冲上来。刘闪满不在乎地笑道:“朕没事,你再去医馆,找几个小口的瓷罐过来!越快越好!”
刘闪没时间吃饭,张星彩也不肯吃。
考虑到她的肠胃不好,刘闪强压着继续试验的冲动,陪着她吃过早膳,然后让婢女找了些极薄的丝帛,费了好大的劲才做好一条粗粗的引线。
刘闪将引线插入罐中,在殿内的花园中找到些极小的石子和瓦砾,将其烘干后与黑色粉末一同混合后装入罐中,罐口用碎布堵住后,又弄了些半干的稀泥继续封紧。
刘闪不知道这颗土炸弹的威力,自然不敢在宫中试验,让黄晧给自己弄了件内侍的衣服,犹豫了一下,让张星彩也换上婢女的衣服,她也没多问。
“黄晧!”刘闪欣喜地说道:“命人准备一辆马车,咱们今天出宫去玩,哈哈哈!”
黄晧听闻要出宫去玩,屁颠屁颠地亲自去准备车马。
张星彩听闻刘闪要带自己出宫,欣喜之余,她也想让妹妹陪同,刘闪自然应允。索性让黄晧召来掖庭令,让嫔妃们自己决定,愿意出宫游玩的都可以同行。
当然,刘闪这样做也有自己的目的:他是想看看那些不知姓名的嫔妃样貌如何,他还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个妃嫔!
刘闪琢磨着,可能还有一些如同张皇后、王贵人那样的妃嫔,她们的牌子,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在自己面前,自然不能凭牌子的数量去猜测。
刘闪毕竟来自一千多年之后,他现在虽是皇帝,但他会尊重每一个女子,绝不会冒然前往妃嫔的寝殿去逐一过目,担心自己若是不喜欢,会进一步地伤害她们。
自汉代起就有“一入宫门深似海”的说法。那些嫔妃入宫之后,生老病死都只能在宫里,至于电视上说嫔妃有“探亲假”,这恐怕也难以考证。
如果受到皇帝宠信的妃嫔还好一些,那些失宠的妃嫔,可能几十年也见不到皇帝一面,更不可能有“探亲假”或出宫的机会,只能孤独地老死在宫中。
后世的名曲《汉宫秋月》,就细致地刻画了宫中女子面对秋夜明月,内心无限惆怅哀怨,对爱情和自由充满着的强烈渴望。
据《后汉书·南匈奴传》记载:“昭君字嫱,南郡人也。初,元帝时,以良家子选入掖庭。时,呼韩邪来朝,帝敕以宫女五人以赐之。昭君入宫数岁,不得见御,积悲怨,乃请掖庭令求行……”
从这记载就能看出,就算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,入宫后也难以见到皇帝一面,一直过着冷清孤寂的生活,只能年复一年的老去。
她听说宫中女子有“与匈奴和亲”的机会后,果断毛遂自荐,宁可远嫁草原大漠的匈奴,也不愿孤独寂寞地老死于宫中。
刘闪也想借此次出行,看看那些妃嫔的意愿,如果她们愿意离开皇宫,刘闪肯定不会阻拦,还会给一大笔铢钱。
本想悄悄出宫玩一玩,现在变成了结伴出游。向宠不敢大意,亲自领着400多名宿卫军护驾,三十多辆马车呼啦啦地出城,声势确实浩大。
刘闪与张氏姐妹同乘一辆大车,心里乐呵着:这个时代的皇帝,恐怕是多个封建王朝中最自由的皇帝;结伴出游不用经过谁的同意,若是前几年,领兵亲征或四处逃难也是家常便饭。
刘闪并未忘记此次出宫的目的,车队沿着官道行出十余里,刘闪让其它车辆先行,自己和向宠悄悄钻入一片密林中。
向宠按刘闪的指示,用随身的佩剑在地上掏出一个小坑。刘闪小心地将罐子埋入坑中,然后用脚将表面踩紧,点燃引线后拉着向宠就跑。
“轰!”
身后一声不大的闷响传来,黑烟尚未散去,刘闪迫不及待地凑上前,顿时兴奋不已。
刚才埋罐子的地方,已经变成箩筐大小的坑,周围拇指粗的树枝被碎石砸断了许多,还有很多碎石深深地嵌在粗大的树干上。
闻声赶来救驾的宿卫军见到刘闪安然无恙,终于松了口气,全都一脸的懵逼,却不敢开口询问。
试验再次成功,刘闪本就没有游山玩水的兴致,也不想扫了31个妃嫔的兴致。
追上张星彩的马车后,刘闪跟她嘀咕了几句,让她们继续游玩,并让向宠保护她们的安全,自己带着几名宿卫军匆匆赶到武库。
刘闪简单地跟张绍提了张皇后的情况,很快就回到正题。
刚才试验成功的只能算不成熟的“土地雷”,它仍然需要点燃引线,根本不可能用在战场上。
刘闪的最终目的,是做一种稍小的“投石车”,能将“土地雷”抛至五百米米以外。
投石车很简单,将现有的大型投石车适当改小就行,关键是这个炸弹本身,它绝不能用简单的瓷罐子,只能用金属外壳。否则,它扔出去还没爆炸就先摔碎了。
刘闪不知道这个时代的冶金工艺如何,也不知道铁罐子外壁的厚薄,只能让张绍联系铸铁工匠,仿照瓷罐的模样制作几个厚薄不同的铁罐。
这个张绍实在太笨,刘闪说了十几遍他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,此时刘闪已经急得满头大汗。
“捷报!”
“捷报!”
“永安大捷!”
……
“永安会有捷报?”
刘闪确定自己没有听错,刚跑出武库就看见几匹快马向宫中疾驰而去,刘闪大叫几声他们都没听见,急忙跳上马车迅速返回。
作者将黑火药提前了300多年,作为本文少有的金手指,仅供各位看官YY娱乐,不必深究。另外,“一硫二硝三木炭”,现代的高中生应该不会陌生,大家看看而已,娱乐就行,勿要尝试。
在刘闪所了解的历史上,众多的史学家以及很多三国爱好者,他们对姜维都是贬多褒少,主要是因为他连年征战,耗损了大汉的国力,却未伤及曹魏的根本。
姜维最后一次北伐时,朝中的文武官员几乎都在反对,就连廖化也多次劝姜维休整军队,认为“连年征伐,军民不宁,兼魏有邓艾,足智多谋,非等闲之辈,建议勿强行难为之事”。
后世的人们,总结了姜维十一次对魏国用兵的结果:其中大胜两次,小胜三次,相距不克四次,大败一次,小败一次;总体来说,姜维的北伐是胜多败少。
从“宏观”上来说,姜维北伐确实造成了大汉“兵困民疲”,这是不可避免的;但同样道理,魏国也有损耗,而且作为战败方的魏国,其损耗远比大汉来得大,在一定程度上,缩小了蜀魏两国之间国力的差距。
正是姜维的主动北伐,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不断衰退的大汉政权。在这几十年里,蜀中土狭民寡,而曹魏拥有九州之地,后者被迫采取战略防守长达三十年,这在军事史上是极为罕见的。
只要一有空闲,刘闪就会仔细回想自己读过的史书,希望找到姜维北伐曹魏“寸功未立”的原因,希望在今后决定性的北伐中,尽量避免相同的失误。
众所周知,大汉后期的将才匮乏,这肯定是个重要的原因。特别是最后几次北伐时,面对强大的魏军,姜维一个人,经常要担负起统帅、大将、参谋的全部职责,可见姜维当时处境的艰难。尽管如此,他仍然能在战术上不断取得胜利。
在刘闪看来,姜维的军事才能,应该不会低于邓艾,正是由于两国兵力和国力的巨大悬殊,以及后勤供给上的困难,这才使得姜维的几次胜利,都难以进一步扩大战果,只能无奈班师回朝。
另一方面,朝中官员的打压也是原因之一。据史书记载:“费祎常裁制不从,与兵不过万人。”也就是说,姜维早期的几次北伐时,手下的士兵还不到一万人,这样的北伐只能是小打小闹,对于魏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威胁。
在历史上,在公元253年之前,姜维一直担任卫将军,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;直到253年费祎被刺身亡之后,姜维才升任大将军,即便如此,他能动用的兵马也不到五万人!
由此看来,要一统华夏,实现自己“大汉万年”的宏愿,必须要对姜维绝对的信任,也要做他坚强的后盾!
天已微明,门外传来有节奏的敲击声,刘闪替熟睡的李昭仪盖好被子,然后轻轻起身。
“陛下,已经查到一些蛛丝马迹,现在可以确定,黄晧跟很多朝臣,及他们的门人常有往来,特别是陈祇!”向宠低声说道。
“陈祇?他是何人?现居何职?”
“陛下,陈祇,字奉中,乃是前大司徒许靖兄长的外孙,其相貌威武,善长多种技艺,深受费祎的赏识。现在,他是费祎府中的家臣。”
听完向宠的调查结果,刘闪略微有些震惊,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否与费祎有关,刘闪觉得,应该查实后再做处理,所以暂时并未表态。
“陛下,除了陈祇之外,他跟阎宇、张表也有往来,经常暗中送钱送物,也有人看见黄晧经常出入景福殿。”
“景福殿?难怪刘理知道得那么清楚!”刘闪冷冷地说道:“不要惊动任何人,继续查!另外,再让人盯着刘永和刘理,一有消息马上来报!”
“诺!”向宠领命而去。
经过前几天的叛乱后,刘闪总觉得有人在背后盯着自己,刘闪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黄晧!但是,刘闪打心眼里不希望是黄晧,因为他确实讨人喜欢。
从向宠初步调查的结果来看,平常唯唯诺诺的黄晧,在暗地里确实有结交党羽的迹象。刘闪相信,如果不是自己先知先觉,黄晧最终肯定会像史书记载的那样:欺上瞒下,操弄威权直至祸乱朝纲。
刘闪并不嗜杀,但为了自己“大汉万年”的宏愿,别说一个宦官黄晧,刘闪不介意杀掉任何人!
冬季的成都异常阴冷,刘闪裹紧宽大的汉袍后回到殿内,今日他不想上朝。在刘闪看来,只要不是魏延、姜维或孟光有事启奏,几日不朝又有何妨?
熟悉三国历史的人,对吴、魏两国的“新城之战”不会陌生,因为这是三国后期规模最大的战役,也是最不对称的战役:吴国诸葛恪的二十万大军攻城三月,仍没拿下三千人驻守的新城。
三国时期,合肥属曹魏扬州淮南郡,由于曹魏和孙吴在江淮流域连年交战,公元233年,魏将满宠分析战场形势后,魏国朝堂经过几番论战,曹睿终于同意建立新城,合肥新城于当年建成。
从此之后,合肥旧城中只有少量的军事人员和设施,合肥新城作为主要的军事据点存在,从234年第一次新城之战开始,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,合肥新城就成了吴、魏两国争夺的重要据点。
不论是古代的冷兵器作战,还是一千多年后的高科技战争,无不遵循“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;粮草未动,情报先行”的理念。
如今,姜维和陆逊在相距不远的秭归、信陵对峙已有月余,双方都没有较大的兵马调动:姜维仍然保持着秭归三万、巴东两万的兵力,与陆逊的八万大军差距并不大。
经过多日的侦查,探马已经确定:吴国正在夷水大兴土木。吴国的战略意图很明显,就是效仿魏国的“合肥新城”,在夷水建一座军事要塞,阻断姜维绕道恩施、长阳进取宜都的通道,确保陆逊部队后方的安全。
姜维与几名将军伪装成狩猎的百姓,登上佷山远远地看到,这座要塞已经初具雏形,其规模暂时比不上合肥新城,因为它只能根据狭长的地形,形成一个易守难攻的天然关隘。
由于蜀军并不擅长水战,湍急的夷水也不适合行船,自然不能绕过这座关隘,只能以步兵强攻。如果这座关隘顺利建成,恐怕蜀兵付出百倍于守军的巨大伤亡,也无法顺利将其攻下。
廖化和邓芝建议立刻出兵,趁它还未建成时将其摧毁,姜维综合考虑后,也觉得应该出兵。
不过,姜维的目的并非将其摧毁,而是促使吴国劳民伤财,并且日夜不停地赶工期,希望它尽快建成!
“这是为何?造几条木筏很难吗?”陆逊不悦地喝道。
吴军连攻两日,仍然没能打通两端的通道,陆逊已经意识到情况不妙,赶紧命人砍树造筏。
然而,两天时间已过,一共才造出三十来个木筏,只够三百人从夷水撤走,陆逊如何能不生气?
“丞相,并非末将偷懒!”一名校尉解释道:“我被蜀军困在这里,南边是湍急的夷水,北面又是悬崖峭壁,无法找到更多的大树啊!”
陆逊咬咬牙并未说话,校尉接着说道:“丞相,若想造出更多的木筏,就需要更多的大树,唯有佷山才有足够的树木。不过,要上佷山,只有沿长杨溪而上,这里却有吴班、吴懿在此驻守……”
陆逊稍作犹豫,提笔写了封信,然后说道:“你把这封信给大将军送去!自然会有足够的木头!”
“诺!”
……
长杨溪下,吴军营寨。
诸葛谨在此扎寨已有好几日,他阻断了佷山上的蜀军与恩施的粮道。
拆阅陆逊的信后,诸葛谨咬咬牙说道:“不错!正合我意!”
“大将军,莫非……陆丞相已有破敌之法?”张承欣喜地问道。
“不,没有!”诸葛谨见张承一脸的失望,冷冷地说道:“我虽被蜀军围在此地,但我亦围住了两万多蜀军!根据时间来看,山上的蜀军粮草已断!纵然我要退走,也得咬掉姜维身上一块肉!”
“莫非,我准备攻蜀军的营寨?”张承惊恐地问道:“蜀军居高临下,我若攻寨,恐伤亡惨重啊!”
“若不攻破此寨,我就无法获得足够的木头造筏!我粮尽之时,伤亡会更大!”
张承点点头,诸葛谨正要下令攻寨,突然听得一声巨响,并伴随着惊恐的尖叫声和呼救声。
“大将军……小心!”
张承猛推了诸葛谨一把,诸葛谨被推到十几步外,一个趔趄摔在地上。
就在诸葛谨刚才站立的地方,一支标枪直挺挺地插在地上。
诸葛谨刚刚回过神,十几名兵卒手持木盾,赶紧将他护住,退到营寨的西侧。
“可恶!实在可恶!”诸葛谨恨恨地盯着山腰。
此时,屯兵山上的关索部队粮草已尽,他按照姜维事先的安排,在吴懿和吴班身后的半坡上,砍倒大树并整平地面,又将五架投石车架设起来,同时,关索也将三十名蹶张弩手,部署在靠近吴军营寨的地方。
前段时间,关索只是听说过姜维的谋略,直到现在,他才真正地对姜维佩服不已:吴兵下寨的地方姜维早就料到,并且计算得丝毫不差!
这几架居高临下的投石车,以及那几十个蹶张弩手,刚好可以攻击诸葛瑾的营寨。
从天而降的巨石和标枪并不多,但寨中的吴兵都不敢轻视,因为这些石头和标枪没有“准头”,没人知道它们会落在什么方。
一整天下来,诸葛谨的寨内乱成一团,每个兵卒都紧绷着神经,随时仰望着自己的头顶,一刻也不敢放松。
然而,诸葛谨却不敢轻易撤走!如果他一旦撤走,佷山的蜀兵与恩施方向的粮道就被打通,再也没有吃掉这块肉的希望。
直到次日傍晚,落石和标枪仍在零星地落下!
此时,关索领着一小队蜀军下山,来到吴班和吴懿的营寨。
“关将军,真是抱歉,咱也没有吃的了!”吴班无奈地笑道。
“不,本将并非下来找吃的!”关索面无表情地说道:“按大将军的计划,应该是今夜子时攻寨吧!”
“不错!”吴懿兴奋地说道:“我等出发前,大将军说会有神兵相助,原来说的就是你关将军,哈哈哈!”
“关将军,吴兵被你这么一闹,全都在崩溃的边缘,他们站着都能睡熟了!等到子时,我只需一声大喝,寨中吴兵必被吓尿,哈哈哈!”
“咦……”吴班奇怪地问道:“这又是何物?”
“连弩!这可是真正的神物!”关索欣喜地说道:“本将出发前,陛下将一百具连弩全都给了本将!”
寨中蜀兵纷纷围上来,关索带来的那些兵卒也不吝啬,全都自豪地演示着连弩的用法,引得众多的兵卒羡慕不已。
“不必羡慕!”关索平静地说道:“陛下说了,不出一年,我大汉的士卒,至少有一万人可以装备连弩!”
关索如此说,那些围观的兵卒不仅没有散去,反而有更多的人围上来,都想体验一下这件神物。
“本将再去睡会儿,子时叫醒我!”
关索说罢,钻入吴班的营帐,只寻到几个空空的酒坛,无奈地摇头,倒头便睡。
……
半夜时分,关索睡得正熟,突然被一声锣响惊醒。
数百名弓箭手如恶狼一般扑向吴军营寨。
此时的诸葛谨和寨中的吴兵,早就被折磨得身心疲惫,他们一听到锣响和喊杀声,全都惊慌失措地往东退去,留下断后的两千吴兵,甚至跑在了最前面。
吴班、吴懿领兵在后面一路掩杀,吴兵几乎没有像样的抵抗,在这狭窄的通道上,相互踩踏而死者不计其数。
“兄弟们,继续冲!杀光吴兵!”吴懿大喝道,令弩兵暂停攻击,示意枪兵靠上去,希望以短兵相接的方式,给吴兵造成更大的恐慌。
“吴将军,现在还不是时候!”关索恨恨地瞪着落荒而逃的吴兵,让他暂时停止进攻。
吴懿下停止追击后,关索说道:“吴将军,我也想杀尽吴兵,但困兽犹斗。若逼得太急,我恐多添伤亡,还是遵照大将军事先的部署更好。”
吴懿,本是刘璋部下的中郎将,归顺刘备后时有战功;230年随诸葛亮伐魏时,曾与魏延在阳溪大破魏将郭淮、费曜,然后升任左将军;诸葛亮病逝后,刘闪遵照遗表,加封其为车骑将军。
吴懿很久没有畅快淋漓地杀敌,眼看仓惶逃走的吴兵,他自然忍不住想大开杀戒;
经关索提醒后,吴懿才想起不能乱了大将军的部署,心有不甘地望着远去的吴兵,下达了停止追击和建造壁垒的指令。
诸葛谨退走后,蜀军的粮道已经打通,廖化很快就送来足量的粮草,也有信使给吴懿送来一封书信。
“叛逆!真是叛逆!”吴懿阅信后,顿觉羞愧难当,咬牙切齿地骂道:“两个畜生!竟敢做出此等谋逆之举!”
“兄长……所为何事?”吴班警惕地问道。
吴懿将书信交给吴班后,突然扑通一声,往成都方向跪下:“谋反大罪,当诛九族!谢陛下不杀之恩!谢陛下不杀之恩……”
吴班阅信后也大吃一惊,赶紧下跪谢恩。
“二位将军,陛下托我转告:一人做事一人当,他不会再追究此事,仍会如亲母一般孝敬太后,二位将军不必顾虑。”
关索说罢,吴班和吴懿再次遥拜谢恩。
……
蜀军并未追来,诸葛瑾在紧邻夷水要塞的西边又筑起壁垒,蜀军在弓弩的掩护下,也在二百步外筑起一道新的壁垒,进一步压缩了吴军的活动范围。
自此,蜀兵一直在己方的壁垒前高声喊话,饥饿的吴兵不停地跑到蜀军壁垒前投降,诸葛瑾已经斩杀试图叛逃的吴兵六百多人。
这里的地形太过狭长,关索只能架起一架投石车,然而,他投向吴兵的并不是巨石,而是几小袋粮食和劝降书。
被围的吴兵确实饿极了,他们抓起大米就往嘴里塞。诸葛瑾没法制止因争抢而引发的骚动和冲突,只能下令将“闹事”的吴兵处以重刑。
“丞相,我粮草已断,每日都有士卒偷跑到蜀军阵前投降,我扎的木筏也被偷走十几个!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啊!”诸葛谨无奈地叹道。
“哼!撑死胆大的,饿死胆小的。”陆逊未置可否。
“丞相,我是不是……”
“食君之禄,担君之忧。”陆逊无奈地说道:“我若撤走,麾下的士卒必降蜀军,尽量再坚持几日吧。”
“丞相,我已断粮,如何坚守?何不早做决断?”
“告诉那些兵卒,就说援兵已在攻打长阳,旦夕即破。这样一来,或许能多挨几日。”陆逊正色说道。
“丞相,士卒们关心的,不是援兵能否到来,而是自己的肚子啊。”
“或许真有援兵呢?”陆逊期待地说道:“我被围在此地,朱桓一定会知道,或许他会引兵来援。只要长阳一破,我就有反败为胜的机会!”
“唉!但愿吧!”
周循,东吴名将周瑜的长子,有周瑜的遗风,深受孙权的厚爱。他不仅被封为骑督尉,还迎娶了吴皇孙权的长女孙鲁班。黄龙元年(公元229年)周循病逝后,孙鲁班又嫁于全琮。
丢了巫县、巴东城和秭归城的全琮、潘濬、孙桓等人回到建业后,他们都未受到责罚,孙权只是令他们在陆逊帐下将功补过。
当然,这并非因为全琮是孙权的女婿,而是孙权明白:姜维是诸葛亮的传人,他用兵诡诈,并且陆逊也在他手上吃过亏。
陆逊一再强调夷水要塞的重要性,全琮立功心切,明里暗里想了很多办法,终于接下这个重任。
孙权亲拨两万兵马给他,并征召民夫一万多人,希望能在元宵节前完工。
夷水要塞位于夷水的北岸,南侧是湍急的夷水,北侧是陡峭的佷山,距离长阳城大约半日路程,过了长阳就是宜都。
因此,夷水要塞一旦建成,吴国只需在此驻扎两千兵,就能轻易阻挡十万蜀兵,恩施通往宜都之路就被截断,陆逊再无后顾之忧。
……
关索按照姜维的指示,引兵五千来到佷山。
“立刻砍倒大树,安营扎寨!”关索说罢,又走到山顶南侧看了看,然后令道:“将这几棵树砍倒,将地面整平!”
罗宪上前几步,往崖底看了看,略有担心地说道:“关将军,我才五千兵马!我一旦发起进攻,吴军必会杀上山,我如何能挡?”
“此地山势险峻,易守难攻,我携了一月之粮,有何担心?”关索不屑地哼道 。
“关将军,话是如此,只是……”罗宪犹豫着说道:“我刚到军中,大将军就令我来此地袭扰吴军,这恐怕……”
“罗将军,不要妄加猜测!本将相信,大将军绝不是那种人!此事不得再提!”
“诺!”
自南中跟随关索以来,罗宪非常了解关索的性格,知道关索不会怀疑任何一个人,罗宪的嘴角动了动,并未继续说话。
在罗宪看来,姜维令关索引兵来此,明显是把关索和五千蜀军当成了诱饵!
从吴军稍后的部署上来看,罗宪并未猜错:
蜀军扎好营寨,整平空地后,五架投石车组装完毕,关索立刻命人将其架起。
此时,山下的夷水要塞一片忙碌,两千多民夫正在紧张地施工。
突然,几块巨石从天而降,砸在工地上轰隆作响,这声音让人无比胆颤。
吴兵和正在修建的民夫刚刚回过神,又有几十把标枪从天而降,引得一阵惊恐的尖叫声,他们赶紧找地方躲避。
这一轮袭击之后,山上的蜀兵再也没有发动齐射,只是偶尔投几个巨石或标枪,这样的攻击没有造成吴军的巨大伤亡,但下方的夷水要塞,再也不敢继续施工。
没人知道巨石何时会落下,没人知道这些石头会砸在何处,没人愿意成为被砸中的“幸运儿”!
“全将军,蜀军何时驻于山上?他们又如何带来的投石车?”孙桓奇怪地问道,警惕地注视着山顶,生怕又有巨石和标枪落下。
“全将军,蜀兵实在太狡猾!他们驻于山顶,居高临下可威胁我,我却对他无可奈何。”周鲂望着山顶说道。
“全将军,你……可是立过军令状啊!”孙桓担忧地说道:“若不赶走山上的蜀兵,很难在元宵节前建成这座要塞,我不敢延误工期啊!”
“可恶!实在可恶!”全琮仰望着山顶,愤愤地令道:“孙桓,引兵两千,屯于要塞以西两里,扎起壁垒,阻挡恩施方向过来的蜀军援兵。”
“诺!”
“周鲂,引兵三千,立刻上山,打探蜀军虚实!”
“诺!”
……
一个时辰后,周鲂顺利地爬上山,接近了关索的营寨,心头暗叫不好:
蜀军营寨的四周,皆有横杠的大树做为掩体,寨外近百米内的大树皆被砍倒。若是两兵相接,寨中的蜀兵居高临下,只需一通箭雨,攻寨的吴兵将很难应对。
事实也是如此,周鲂发起两次试探性的攻击,吴兵损了几十人,却无一个人能靠近营寨,寨中的蜀兵无一伤亡。
周鲂报回蜀军的部署,全琮苦无破敌之法,只好派人向陆逊请教;陆逊听闻佷山上有一支蜀军,于是连夜来到夷水要塞。
“本相一直注意着秭归和巴东的兵马调动,佷山上的蜀兵,很可能来自永安!”陆逊狐疑地问道:“有多少兵马?何人统领?”
“兵力大约四到五千,至于领兵之将,暂时还不清楚。”全琮如实回答,随即又担心地问道:“丞相,可有破敌之法?”
“现在是冬季,雨水稀少,就算山顶扎寨的蜀兵粮草充足,他们仍然需要大量的饮水。要破蜀军,其实不难!”陆逊自信地说道:“蜀军取水之地,必是长杨溪!”
全琮心头大喜,陆逊继续说道:“传令:孙桓,领兵三千,驻于长扬溪,阻止蜀兵下山取水;周鲂,领兵三千,在下山的必经之路设伏。”
陆逊令罢,诡异地笑道:“如此一来,蜀军断水,不能久持,不出十日,必然退走!届时,我再布兵马,趁机全歼!”
两人领命而去,陆逊在全琮的恭维声中,冒着不时落下的巨石,视查了要塞的施工进展,然后在要塞以东搭起帅帐。
当夜。
孙桓在溪边搭起营帐,直到半夜,也没见到有蜀兵来此取水。
孙桓正怀疑陆逊的判断是否有误,突然听得一阵喊杀声,欣喜地跑出帐外。
“嗖!”
一支火箭擦着孙桓的鼻子而过,直直地插在旁边的一个营帐上,大火瞬间点燃了这顶帐篷。
孙桓赶紧后退几步,这才发现营寨内已是一片火海,四面都有火箭不停地飞来,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数十名吴兵。
孙桓扎营的地方,位于低洼的溪边!
孙桓曾向陆逊建议将营寨扎在坡上,但陆逊坚决反对,孙桓只能奉命行事;眼下,蜀兵居高临下,这营寨如何守得住?
孙桓狠狠地咒骂着陆逊,未做抵抗就下令退兵。
孙桓回去见过陆逊,却见周鲂也灰头土脸的退了回来,并且损了一千多人!
陆逊见状并未生气,笑呵呵地招呼两人入座,并亲自倒上米酒。
“二位将军辛苦!我这“招投石问路”已见成效!看来,我估计得没错:姜维在佷山,至少投入了两万兵马!”
“两万?何以如此肯定?”全琮疑惑地问道。
“诸葛亮用兵谨慎,姜维却喜欢兵行险招,但他也会险中也会求稳。”陆逊喝了一大碗酒,然后说道:“蜀兵孤军驻扎在佷山之上,姜维必会保证他们的水源和退路的畅通。我让二位将军截他水源和退路,这不过是试探而已。”
周鲂和孙桓一语不发,陆逊继续说道:“我已探明:佷山之上,蜀将关索驻兵五千;长杨溪边,由蜀将吴班守卫水源;夷水以西,由吴懿扎下壁垒保证退路;其中,吴班和吴懿各有八千兵马。”
“既然如此,那……我该如何破敌?”全琮急忙问道。
全琮最关心的,就是这座要塞能否按时完工。
“将军勿急,其实,我早就料到姜维会来!”陆逊自信地笑道:“吴班和吴懿领兵到达后,我已暗中令陈表引兵一万驻守恩施,另有吕壹的一万兵马,屯于恩施以东的夷水隘口,我已截断蜀军的退路!”
“丞相,这样部署,确实包围了两万多蜀兵,但他们的粮草至少能坚持半月!我坐等他们粮尽也不是办法啊!这座城塞的工期,不可拖得太久!”
“将军勿急!就算拖个二十天,这座要塞也能如期完工。况且,要吃掉这里的蜀军,我只需十五日就够!”
“可是……”
“不用可是!据细作回报,目前,蜀军一共才十一万兵马。其中汉中部署四万,姜维手上只有七万人;只要我能歼灭这股蜀军,姜维必定元气大伤!届时,我再取巴东就易如反掌,秭归城也将孤木难支,姜维再狡诈又能如何?”
陆逊说罢,又安慰道:“我会向陛下上表讲明情况,延误工期之事,全将军就放宽心吧!陛下定然不会怪罪!”
“这样最好!”全琮嘴上说着,心头仍有疑惑:“只是……姜维诡诈,万一有什么变故,咱很难向陛下交待啊!”
“哼!”陆逊不屑地哼道:“这夷水狭长,不适合大军展开。我只要堵住两端隘口,蜀兵插翅也难飞!况且,我已令张承、诸葛瑾领兵两万来援,这会儿他们已到宜都,明日午间就能到达此地。”
陆逊说罢,突然将酒碗猛地拍在案上,狠狠地喝道:“我就不信了!我六万兵马,难道困不死两万蜀兵?”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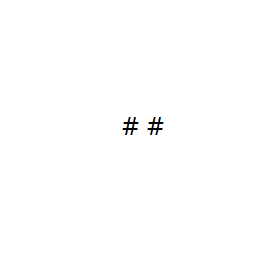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