男女主角分别是杨报国魏忠贤的女频言情小说《九千岁外孙小说》,由网络作家“杨报国”所著,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,本站纯净无弹窗,精彩内容欢迎阅读!小说详情介绍:七个庄子,原来的庄头,加上汪文言提拔起来的一批人,已经越来越有模有样。上午。人们找田地里干两个时辰的活,肚子已经饿得受不了,每处庄子里就开伙了。今天开始。原来的稀饭改成了香喷喷的干饭。桌子不够,人们蹲在地上吃。庄子里的大米已经不多,还是原来大户人家地窖的储藏积蓄,因为京畿地区是漕运的终点,有大量南方的稻米,所以不像西北地区主要就是面食。今天吃的是疙瘩汤。和好的生面用手掐成团块状,下入水烧烤的锅里,煮熟后就是疙瘩汤。类似唐宋时期的胡饼做法。“说好的干饭,变成了疙瘩汤。”“吸溜。”有人边吃边抱怨。王本当做没听见,最快的速度吃完,然后去排队,重新吃第二碗。那人看见王本的动作,气愤的闭嘴,也不再抱怨,埋头只管吃,吃完了也跑去排队,生怕锅里没...
《九千岁外孙小说》精彩片段
七个庄子,原来的庄头,加上汪文言提拔起来的一批人,已经越来越有模有样。
上午。
人们找田地里干两个时辰的活,肚子已经饿得受不了,每处庄子里就开伙了。
今天开始。
原来的稀饭改成了香喷喷的干饭。
桌子不够,人们蹲在地上吃。
庄子里的大米已经不多,还是原来大户人家地窖的储藏积蓄,因为京畿地区是漕运的终点,有大量南方的稻米,所以不像西北地区主要就是面食。
今天吃的是疙瘩汤。
和好的生面用手掐成团块状,下入水烧烤的锅里,煮熟后就是疙瘩汤。
类似唐宋时期的胡饼做法。
“说好的干饭,变成了疙瘩汤。”
“吸溜。”
有人边吃边抱怨。
王本当做没听见,最快的速度吃完,然后去排队,重新吃第二碗。
那人看见王本的动作,气愤的闭嘴,也不再抱怨,埋头只管吃,吃完了也跑去排队,生怕锅里没有了。
今天敞开了吃。
每人都能吃几大碗。
各个吃的肚子圆滚滚的,发出惬意的声音。
肚子好久没有这种沉甸甸的感觉了。
许多人都忘记了吃饱的滋味。
“吃完了赶紧休息,下午好好干活,你们自己数数,你们都吃了多少粮食,不好好干活,对得起吃进肚子的粮食吗。”
王本放下碗,打了个饱嗝。
然后不忘记交代。
“明天还有吗?”
有人期望的盯着王本。
王本点点头,“明天吃面条。”
众人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。
无论是谁。
此时心里都很高兴。
……
“这一顿下来,那些汉子每个人至少吃了一升面,如此还得了。”
王本吃饱了肚子,休息了片刻。
回过头来就找到汪文言,说出了自己的担忧。
仿佛忘记了吃的时候,谁是最积极的。
西平村本地村民有两百五十三口,灾民也有两百多口,光劳力就有近两百号人。
这些人一顿就吃了两百升的口粮,还要其余的妇孺老人小孩,一天下来,哪怕下午吃稀饭,也得需要六七石粮食。
一个月就是一百八九十石。
七个庄子,每个庄子都比西平村大,特别是上马村下马村这几个。
王本算了下账,七个庄子一个月需要两千四百多石粮食。
“要不了多久,有两万石的粮食抵达庄子。”汪文言笑呵呵的说道。
“两万石?”
王本吸了口气,然后询问道,“丁源的儿子去干的那件差事?”
得到确认,王本忍不住感叹。
“少爷真是了不起啊。”
“也只有少爷这能有这样的大手笔,一口气就能弄来两万石粮食。”
王本无法想象两万石的粮食堆积在一起是什么样子。
汪文言也很佩服。
大灾之年,谁也不容易弄到大笔粮食。
哪怕是朝廷都很艰难。
福王有粮食,可谁能让福王拿出粮食来呢。
皇上都不行。
结果杨报国此子做到了。
汪文言大致清楚杨报国的做法,只能说此子的眼光极其的敏锐,竟然能抓住别人看不见的机会。
借助郑贵太妃,既稳定了他祖父在内廷的权势,又能获得两万石的粮食。
明明这么小的年纪,却比许多朝堂老人都要懂得人心算计,连自己都不服不行啊。
此时。
几名工匠正在田埂上摆弄三脚耧车。
“人很难拉动,必须使用牲口。”老匠户双手一摊,看着几位气喘吁吁的徒弟,向身旁的管事说道。
“现在庄子里最缺的耕牛,每头耕牛每日耕三亩地,隔几日一歇。”
管事指了指远处天边的大山。
“那里还在搞梯田,总共才不到三十头耕牛,连耕种都不够,怎么可能拿一头牛来呢。”
“这可怎么办?”
老匠户也没有办法。
这件事最后还是到了汪文言那里,汪文言知道此事的重要性,让王本去处理。
王本和匠户约定了时间,准时的牵了头牛来。
“这牛今天歇息,这里的活不重吧?”王本一脸的担心,这是他能想得到的办法。
只能苦一苦这头耕牛了。
“不重,就试试。”
老匠户说道。
然后他的徒弟们把家伙什放在牛脖子上,琢磨了一会,终于开始。
王本也很好奇这三脚耧车,留下来观看。
“这玩意难不难。”
“不难。”
“不过需要时不时的检查一番,特别是这耧腿,安装的不好,种子漏不下来,播种不均匀,这个耧就废了。”
耧车主要是木头制造,除了划入土地的耧铧部分使用铁料,打造的锋利和坚固,深深的插入泥土中。
年轻徒弟热情的解释。
王本一路跟着。
只见他们把种子放入一个篓子里面,篓子底部有漏口,漏入到三个耧腿,通过耧铧种下。
随着耕牛的拉动,轻轻松松就把种子种下去。
王本蹲下来查看。
种子种的深,不比人干的差。
忍不住大奇。
这玩意速度快,又轻松,哪个神仙弄出来的,怎么没听过呢。
不过王本很快发现了不对。
“诶,这漏种的厉害啊。”王本看到有一条腿,很长的一段没有种下种子。
经过王本的提醒,学徒连忙停了下来。
老匠户推开徒弟,趴在地上找问题,他的几位徒弟老老实实的跟在师傅后面。
“这耧车有问题。”
王本摇头晃脑,“难怪没人用。”
老匠户不开心了。
这耧车是他造出来的,岂不是说自己手艺不行。
老匠户也是臭脾气。
“走走走,都在这里挡住别人干事。”
把人赶走了。
老匠户骂了徒弟们一通,这才专心致志的寻找问题,从上午到下午,还让徒弟们把耧车搬回去,晚上打着灯火。
到了第二天早上。
老匠户得意的找到王本,拉着王本去田地里。
“你这老头,我事情多着呢,哪里有闲工夫陪你。”
老江湖力气大。
还有徒弟们帮忙,王本无可奈何。
田地上,已经准备好了耧车,还是昨天的耕牛,重新开始耕种,王本下田跟了一路,啧啧称奇。
“厉害啊,老师傅。”
“男人得有蛋,看到这玩意没有,昨天没给它装上这蛋蛋,它就装孙子了,今天给他装上,你在看。”
老匠户满脸得意,指着耧车下的一颗圆球。
随着耧车的前进,这颗圆球一晃一晃的,把种子均匀的拨开,保证每个耧腿都能有种子分拨下去。
“耧蛋蛋。”
看着那颗圆球,王本大笑,拍手笑道:“原来这耧车是个爷们,您老人家竟然忘记了跟他装蛋蛋,难怪他发脾气,要是我我也得恼火。”
“哈哈。”
老匠户的徒弟们纷纷笑出声。
汪文言甘拜下风。
他心服口服。
自己的胸怀远不如那十四岁的少年。
以前少年做的许多看不懂的事情,汪文言突然看懂了。
少年与民争利。
可少年又没有获得利。
相反,少年用了不少的关系来投入。
现在,汪文言明白了。
虽然不太认同少年的预测,比如大明要亡天下,可汪文言愿意继续赌一场。
就像当下赌秋天的时候仍然还有灾情。
汪文言内心不是滋味。
他既不想少年预测对了,可是他又不敢说少年测错了。
无论是哪种。
汪文言看来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。
他只能做好自己的事。
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五月初。
各处庄子里陆续耕种,只剩下不到两成的田地还在继续耕种,但是已经有了更多的人手可以使用。
不过耕种完了,事情还有很多。
各处的水车开始轮流使用。
往田地里引水。
大人小孩整日踩在水车上,一瓢一瓢的水就这样,积少成多的通过沟渠为庄稼提供水。
小孩子们腿脚酸痛,一边哭一边踩踏。
大人们被集中起来去开垦荒地。
马坊村多了一处铁匠铺。
建在河道旁。
大工匠张九年亲手打造了水车。
从兵仗局请来的老工匠,带着徒弟们垒起了炉子,露天的高炉低矮简陋,是用来冶炼铁料,为各庄的工具修修补补。
土胚搭建的高炉,也就比人高些,旁边撘了个棚子,棚子下方的地上挖了一方凹槽,高炉炼化的铁汁会流入到这里,为了避免下雨,才特意搭建了棚子。
土胚高炉的周边,有一座堆积起来的铁矿山,还有几堆较小的料山。
这些加入冶铁过程中的杂料,是兵仗局来的大师傅手里的不传之秘。
更有高炉炼化铁水的火候,以及用料的比例等等,那是打死也不会说的。
这位大师傅是兵仗局里头最有名的老师傅,杨报国亲自要来的。
他锻造出来的铁器,只要有料可以足够提供,又坚固又耐用,成为了庄子里开垦荒地最好的工具。
“李师傅。”
“在庄子里呆的可满意?”
铁匠铺日夜开工。
李奇的徒弟们轮流打造。
扑面而来的热气,杨报国仿佛没有感受到,恭恭敬敬的上前关心的问道。
“还好。”
“不错。”
李奇笑道。
可以吃饱饭,也受人尊重。
其实李奇心里是不愿意来的,不过这位京城有名的小贵人客客气气的请自己出山,李奇也不好拒绝。
杨报国松了口气。
无论是张九年,还是眼前的李奇,那都是有大本事的人,对于有大本事的人,杨报国认为他们就应该要过得好一些。
倒不是人分三六九等。
而是奉献不一样。
大户们本身就是百姓们身上的蛀虫,而张九年和李奇不同,他们每个人的作用,哪怕用一千个一万个老百姓也无法做到。
这样的人,对于老百姓只有好处。
所以应当格外的尊重些。
哪怕老百姓也是这么认为的。
“庄子里开垦需要的工具越来越多,而工具容易破损,影响庄民们干活的效率。”
杨报国客气的说道,“李师傅如果不嫌弃,我想从庄子里挑一些身强力壮,头脑聪明的后生拜您为师,李师傅可愿意?”
李奇下意识的不愿意。
自己的徒弟已经不少了,出师的就有好几批。
“不如这样,我让人把后生送过来,由李师傅自己挑选,挑出李师傅满意的徒弟。”
“一定要尊师重道,懂得孝敬师傅。”
杨报国不给李奇拒绝的机会,连忙又说道。
既然这般。
李奇倒也不是很反感了。
他最怕教出逆徒。
自己倒不缺三瓜两枣的,只要徒弟们能听话,不把自己的名声给毁了,懂得报恩,多收一些徒弟倒也无所谓。
见对方答应,杨报国松了口气。
之前王本来开口,被李奇拒绝了,自己做足了功夫,就怕李奇也拒绝了自己。
倒不是怕丢脸,而是影响庄子里的事情。
工具是最重要的。
没有工具什么都干不成。
开荒的时候,寻常的镐头,使用个几日就容易出现豁口,而李奇冶炼出来的铁器,应该属于钢的一种了,效率增加了远不止一倍。
毕竟是兵仗局的老师傅。
大明制作鸟铳以及佛郎机的材料,后世学者根据遗传的图纸和冶铁方式,得出结论一种是低碳钢,一种是高碳钢。
变化的来源就是李奇使用的那些杂料,以及对火候的控制,在冶炼的过程与铁水发生了元素变化。
杨报国打量了一眼。
土胚风炉的左下角专门留出一个洞,里面安置风炉。
风炉熔接一根铁杆伸出到外面,然后固定在竖起的石磨上凸起的一块,形成了一个轴承。
石磨下面有托盘,让石磨悬空,石磨的另外一边有一条铁杆。
河边两人高的水车,也伸出一个杆子,杆子与石磨的杆子斜着用铁环连到一起。
河流的水力下,水车不停的运转,又带动了竖起的石磨转动,为鼓风机带去了源源不断的动力。
鼓风机则把空气大量的送入了高炉中,大大提高了高炉中的热度。
这结构可不简单。
结合起来的效率更是不得了。
这位老师傅请的实在是值。
光眼前的作坊,杨报国就另眼相看。
不久。
各庄送来了许多后生。
皆是身家清白,有同乡作保,一家子在庄里干活的子弟。
庄子里这许久以来,已经形成了分工。
人们最想去的地方并不是当管事。
管事过得也苦,与他们吃住是一样的,只是不像他们需要下地干体力活。
最好的是工匠。
张师傅的作坊,还有这位李师傅的作坊。
不光每日吃两顿干饭,地位也高,有什么要求,庄子里都得尽量满足。
许多的后生一脸期待。
李奇挑了又挑。
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好后生,李奇也很高兴。
“师傅。”
一批后生跪下来向李奇磕头。
李奇笑的合不拢嘴。
他可带不来这么多徒弟,不过隔壁的老张想了个好主意,他盯着大徒弟们,大徒弟们带小徒弟。
这老家伙竟然当起祖师爷来了。
岂不是比自己辈分还高。
李奇也学了张九年的法子,也做起了祖师爷。
魏忠贤是个混账性子,也生怕自己的外孙与自己一样,也是个混账的性子。
一般人家要是有这样的子弟,早就要动手教育了,但是魏忠贤不敢。
他真怕自己死了,这小子不跟自己戴孝。
虽然当初让亲人不要来京城,在乡里享受富贵就好,自己一个人在京城闯荡。
结果老魏家的人真不来。
大哥一家子在乡里只享受富贵,魏忠贤嘴上不抱怨,内心还是有些失落的。
没想到亲外孙来了。
这才是身上流着自己血的后人。
所以魏忠贤有时候哪怕被这小子气的暴躁,可心里还是很疼爱外孙的。
“外祖。”
“我没钱了。”
福王的粮食,不会白送给自己。
需要钱。
魏忠贤有钱。
杨报国不光是得罪了御马监老太监的事,主要还是来向魏忠贤伸手要钱。
魏忠贤大怒。
“你个败家子。”
“这个月你拿了几回钱了?”
“我花了呀。”
杨报国理直气壮。
魏忠贤苦口婆心,“杂家的东西,日后都是你的,可是你也不能败家啊。”
“全天下的太监都在向您老人家孝敬,我就算多么败家,恐怕也没外祖您捞的快。”
“杂家花销大,为了哄万岁爷开心,想尽了办法,这些都需要花钱,还有让下面的人办事,要把下面的人喂饱。”
“我也要办事,我也要养人,孙儿又没有正经的进项,不找外祖要钱,还能去找谁要呢。”
杨报国当即说道。
魏忠贤无语。
又感到可笑。
“你眼里就你那两万亩地的事,还有旁的事?”
“外祖要哄皇上开心,小子是不是出了力?”
“客奶奶那边,小子是不是也上了心?”
“还有郑贵太妃,如果不是我的主意,外祖您自个说说,您能这么快掌握内廷?”
杨报国一一说道。
好嘛。
经过外孙如此一说,魏忠贤才醒悟,不知不觉间,自己这外孙的确做了许多对自己很重要的事。
“你要多少?”
自己的权势越来越大,外孙的胃口也水涨船高,魏忠贤不敢像以前一样,任由外孙去拿钱,而是先确认数字。
“两万两。”
“多少?”
魏忠贤不可置信。
“一万五千两也行。”杨报国也知道两万两太多了。
倒不是魏忠贤没有两万两银子,只是谁送东西,也不会只送银子,大多数是珠宝字画珍品人参等名贵物品。
两万两银子,魏忠贤有可能真拿不出来。
毕竟还不是九千岁。
“一千两。”
魏忠贤不想听外孙的话,补充道:“爱要不要。”
去年的粮价是一两银子两石粮食,今年的价格已经开始大幅上涨,如果福王答应卖粮食给自己,哪怕是按照去年的行情,是一笔不小的花费。
杨报国估算过。
顺天府以及京城,人口将近一百四十余万,受灾的百姓至少二十万,杨报国救助不了这么多灾民,十分之一都很难。
两万人,还要劳作,油水不足,干活的壮劳力,一天至少要吃两斤口粮,真要是敞开了吃,三四斤打底。
汉代供应士兵的口粮标准,有记载是每名士兵按照一天吃三斤来供应。
杨报国供应不起。
壮劳力干重活,一天吃两斤,半大小子吃死老子,同样需要的口粮不是小数目。
老人妇孺少吃点,虽然也要干活,只能每人一斤维持不饿死。
而且也没指望这帮人能打仗,当下先活下去才是正经。
连活下去都无法满足,拿什么去打仗。
内地遭灾。
努尔干都司也遭灾。
可努尔哈赤能撑过来,因为建州供应内地的人参贸易,加上李成梁的支持,所以努尔哈赤可以借助人参,获得内地大量的粮食兵器等物资,实力与经济得到了补充。
反之。
大明投入辽东的力量,因为距离还有人的原因,十成的物资,最终能落到辽东的不足一成。
此消彼长,后金的胜利,也成为了必然。
现在吞并了辽左。
他们不会去管辽东的灾民,只需要壮大自己的基本盘,因此实力能直线上升。
反观大明内地。
经济破产,天灾人祸,民不聊生,指望饿着肚子的人去战场上打仗,能打胜仗才是奇迹。
所以不能奢望奇迹。
大明的体量很大,可已经输了几次,没有什么本钱了。
每输一次,都会让局势越发无法挽回。
想要打胜仗。
首先是让士兵吃饱肚子。
十几万吃饱肚子的士兵,加上充足的训练,战场上保持不大败,经过数年的磨合,成为可以野战的精兵。
而背后又是近百万的家属,加上武器装备,马匹草料的民夫,工匠等等个,这无疑是极其困难的。
根子还是萨尔浒。
打败的一方。
内部的问题就会越发严重。
变成了病上加病。
两万亩的土地,春耕秋收,需要几个月的时间,这几个月的空挡,杨报国需要大量的粮食。
朝廷从地方弄不来粮食。
准确的说。
朝廷只能勉强征收供应辽东的军粮,解决不了灾民需要的粮食,连京畿地区的灾民都顾不上,何谈地方上无数倍的灾民。
杨报国还知道。
明年的时候,京畿地区很快就会发生民乱,涉及到山东和京畿河间府。
人们吃不饱肚子,必然会闹事。
山东白莲教要出现了。
无疑为大明雪上加霜。
如果这个白莲教明年造反,能推翻大明,杨报国倒也愿意带头投靠。
可正因为知道现在的大明,还不是民变可以推翻的。
就算自己加入,也只会让京畿地区彻底混乱,不但于事无补,还会让灾民几何倍的变严重。
成为亡天下致命的原因,岂不是与自己的愿望背道而驰。
所以还是只能指望自己。
可魏忠贤不愿意给钱怎么办呢。
魏忠贤现在最在乎谁?
客氏。
因为只有客氏帮助,魏忠贤才能掌握皇帝朱由校的信任。
那怎么让客氏帮自己说服魏忠贤呢。
找到客氏的软肋。
客氏的软肋是什么?
还是皇帝。
皇帝要成亲了,客氏又是拉拢郑贵太妃,又是拉拢魏忠贤,甚至连自己的身子都卖给了魏忠贤。
可见客氏有多么害怕皇后。
俗话说得好,挡人财路,犹如杀人父母。
天灾的时候,是地方上的大户土地兼并,侵占生产资料最好的时机,这个时候,有人要和他们抢,那不得拼命。
魏忠贤忙得焦头烂额。
京城里对魏忠贤的骂声越演越烈,魏忠贤何时见过如此的态势,比起以前的动静,实在是小巫见大巫。
魏忠贤又后悔,又担忧。
“说起来也怪,万岁爷最近对咱是越来越好了,咱说什么,万岁爷都答应。”
“那是因为外头的人反对外祖您越激烈,皇帝才会对您越放心,更愿意放权给外祖。”
杨报国放下筷子说道。
魏忠贤愣住了。
他倒是没从这方面想过,经过外孙的提醒,魏忠贤把许多事想通了,原来是这样。
魏忠贤默默的咀嚼嘴里的羊肉,又喝了一口汤,突然问道,“如果咱找万岁爷要东厂提督如何?”
“现在不是好时机。”
“为何?”
“外祖您还准备杀王安吗?”
“当然要杀,此人威胁太大,打虎不死必受其害,可不能妇人之仁。”魏忠贤立马说道。
“既然外祖仍然要杀王安,您前脚向皇帝要了东厂提督,后脚就把司礼监王安杀死了,您说皇帝怎么想?”
如果面对的是迷雾,没有人可以看透未来。
但自己不同啊。
借助自己的知识,对整个大明官场的脉络,乃至皇宫的情形的了然,杨报国敢说自己第二,就没人能说第一。
无论是魏忠贤的想法还是行为轨迹也好,朱由校也好,客氏也好,他们在自己的眼里没有秘密。
他们内心的想法,以及会采取的做法,都能被自己提前看透。
魏忠贤习惯了外孙的眼光,又一次的被说服。
暗中侥幸。
幸亏这样的人是自己的亲外孙,要是自己的敌人,想想都感到可怕,太聪明了。
聪明的有些吓人。
“也是,反正东厂现在也听杂家的,左右不过虚名罢了,迟早还是杂家的。”
魏忠贤点点头,不再打算现在就把东厂提督弄到手。
“下雨了。”
“下雨了。”
突然。
门外传来惊呼。
周进激动的跑进来,手舞足蹈的大笑,说外头下雨了。
杨报国已经听到了动静。
屋子里的小黄门都纷纷向外面望去。
这场雨终于下下来了。
魏忠贤脸色变得难看,他担心会影响自己从灾民手里暂收耕牛的事情。
灾民是死是活,魏忠贤可没放在心上。
耽误了自己揽权却不行。
真要是灾情熬过去了,要不要强行征收呢,魏忠贤脸色越来越阴沉,已经打算继续动手。
管你天灾不天灾。
天灾了,要收灾民的耕牛。
没有了天灾,那就收百姓家的耕牛。
至于百姓家没有了耕牛,没办法好好种地,魏忠贤可不管。
杨报国脸色同样不好。
这老天真是不给老百姓活路啊。
如果一直旱,老百姓必然会准备,拼死一搏,想方设法的去找活路,哪里有活路就往哪里去。
大明这么大,就像一条沾了水的毛巾,使劲的去拧,总能挤点湿气浮出。
可偏偏现在下雨了。
老百姓们以为灾情已经过去,高高兴兴的放下了戒备,勤勤恳恳的的耕种。
北方的麦子在三四月耕种下去,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照料,到了六七月就能收获。
辛辛苦苦忙活几个月,不就是为了秋日的丰收么。
但是老天爷开了个大玩笑。
杨报国清楚的知道,史料是这么记载的:三伏不雨,秋复旱。
这比春耕的时候不下雨要更可恶。
不但老百姓没有防备,官府也措手不及,整个大明都被这极端的气候打了个全军覆没。
辛苦了一年,人也累废了,正是需要吃一口饱饭恢复点元气的时候,结果颗粒无收。
官府也没有防备,想要从南方调粮都难。
结果就是明年。
山东开始造反。
京畿地区也开始造反。
一场巨大的打击,导致辽东形势越发的严峻,最后再一次全军覆没,让后金再一次壮大。
同样。
对自己的计划也会造成巨大的影响。
杨报国不再停留京城。
后日皇上的大婚,自己身份低,没资格在前台露脸,杨报国带着工匠们去了庄子。
……
“下雨啦。”
百姓们狂欢。
许多人准备返乡,虽然没有多少积蓄,可是勒紧裤腰带,熬上几个月,等到秋天的收获,苦日子总算是渡过去了。
往年都是如此的经验。
七个大庄子都受到了影响。
灾民们要离开。
庄子里不放人,老王头威胁道:“你们与庄子签了契约的,是你们说走就能走的吗。”
众人面面相觑。
“当初没有活路,我们被逼无奈才签这份把人当牲口使唤的契约,可是现在有了活路,你们凭什么不放人,”
“对。”
有人附和,骂道:“每天干那么多活,结果连饭都吃不饱,是想把俺们给累死啊。”
“扒皮黑心,就没你们这般狠毒的。”
原来的灾民们纷纷破口大骂。
当地的百姓也同仇敌忾。
老王头威逼利诱,庄子里的管事们也出言相劝,可好说歹说,就是没有多少人愿意留下来。
人多势众,老王头挡不住。
几个庄子每日都有人拖家带口的逃离。
隔壁下马村的老陈心善,下马村跑的人最多。
汪文言仿佛不知道。
“大揽总,各处开荒,还有上马村平整土地,现在都没了人手,难道就半途而废了?”
王本不明白大揽总为何像变了个人似的。
汪文言无奈。
“天要下雨,娘要嫁人,谁能挡得住,由他们去吧。”
“那可不行。”
突然。
门外传来了冷哼声音。
杨报国带着一行人闯了进来。
汪文言露出意外的眼神,不过很快又恢复平静,就像当初在诏狱里一样的神情。
杨报国打量了汪文言两眼。
上次猜测此人只是为了庄子,并不是效忠自己,看起来自己没有猜错。
“大千。”
杨报国喝道。
“在。”
“把逃离庄子的人抓回来,严惩不贷,到时要看看,还有谁敢继续逃跑。”
当初登记灾民的时候,每个乡的人集中在一起,会安排相对于轻松的事,所以许多灾民主动找到同乡作保,证明自己的身份。
这些册子在手,没人跑的了。
汪文言不能理解。
根据前段时间的相处,汪文言认为眼前的这位少年,应该不是不近人情的人啊。
“半年。”
“为庄子干半年的活,只要灾情真的过去了,庄子里补偿他们,并且恢复他们的自由。”
这是自己的心里话。
杨报国一脸认真。
汪文言明白了,如果是这样的话,他愿意支持。
汤山在北,挡住了寒风。
沙河、榆河、白河几条河流绕开汤山,在汤山的南边形成了一个几字带。
适合的气候,加上丰富的水源,两百多年来的恢复,重新开垦了许多的土地,最后养活了许多的百姓。
人们在这片土地上休养生息。
不知道从哪天起,人口增加了,能收获的粮食却越来越少。
“这里。”
“还有那里。”
一名管事带着十几名农夫,手里拿着铁锹锄头,还有镐头等工具,管事交代众人在这里平整土地。
“这可不是好地方。”
有位年纪大的农夫观望了四周,然后有些忧虑。
这里的确有不少的荒地,可是地势不太好,就算平整土地后修建了沟渠,也很难形成自然的水流。
那时候需要用水车。
这样的田地收获不多,又比一般的田地更难伺候,花费老大的力气,才能有不多的收成。
“有好地早就开荒出来了,能开垦出水浇地就不错了。”
管事的话,打消了众人的意见。
十几名农夫没有耕种,一直在各处平整土地,已经具备了丰厚的经验。
他们有好几支队伍。
有的队伍专门平整土地,有的队伍专门在平整好的土地上挖沟开渠引水。
最累的是在山上干活,那里要打造梯田,是活最苦的地方,不过多半安排的是那些没有同乡互相作保的“孤魂野鬼”。
众人已经习惯了,顶着太阳开始干活。
几名农夫开始挖土。
只有一辆推车。
等他们做完了初步的活,其他出的队伍腾出手来,这里的人就会变多。
每位农夫都是干活的好手。
不光把活干的快,还能干得好,看起来是平常无奇的事,就如耕牛一样,从小的时候,已经学会了劳作的技术,深深烙印在骨子里。
“噗。”
一名十五六岁的后生,把堆积的土块铲到推车上。
“再装点。”
见后生停止了动作,推车的汉子吩咐道。
“爹,干嘛这么辛苦。”
原来推车的汉子是这位后生的父亲。
汉子满身是汗。
“力气是用不完的,今天的力气用完了,明天就又又有了,俺们庄稼人不能浪费力气。”
汉子平淡的说道。
以前祖父也是这么说的。
后生张了张嘴,最后沉默了,按照父亲的吩咐,往推车里铲了更多的泥土。
汉子把泥土运到别处,然后继续回来装运。
一直干了两个时辰。
所有人都累的。
又累又饿。
从别处忙完赶来的管事,见到此地的进度,满意的露出笑容,告诉人们回庄子里吃饭。
到了饭点。
各处的队伍纷纷回来庄子里。
庄子里的妇人们已经做好了今日的午饭。
“今天又只有米糊糊。”
看到大锅里的食物,众人露出了不满。
米糊糊撑肚子。
但是不扛饿。
干上一个时辰的活,肚子就饿得呱呱叫了,下午的饭又是稀饭,许多人饿得受不了。
后生跟在父亲身后。
汉子默默的排队。
队伍里有许多这样的人。
端着碗,汉子也不走远,蹲在棚子外面大口的吃,后生和汉子的动作一模一样,就像刻画出来的。
“吸鲁鲁。”
“咕噜噜。”
这一片都是蹲在地上喝米糊糊的农夫。
他们吃完了后,又赶忙重新去排队。
米糊糊做的很多。
每个人能吃几大碗,也只能吃几大碗,这玩意就是如此撑肚子,却又不扛饿。
“也不知道娘和弟弟妹妹们在干嘛,他们吃饱了没有。”
把碗筷交回去。
后生跟在父亲身后嘟囔。
吃完了饭,有半个时辰的空闲,这个时候,人们会找个阴凉的地方午睡,缓解身上的疲劳。
汉子来到一棵树下,躺下就睡着了,发出巨大的鼾声。
后生睡不着。
挂念自己的娘和弟弟妹妹们,想着想着也迷迷糊糊睡着了,刚刚睡沉,却被父亲叫醒。
后生揉了揉眼睛,张了张嘴,最后摇头晃脑,继续像往常一样,默默的跟在父亲身后。
“以后早点睡,别东想西想的。”
汉子交代。
“哦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
就是这般。
两父子又过了一天。
不过今天和往常不一样。
在人们吃完下午饭后,管事出来告诉人们,村子里已经腾出了办社学的房子。
以后孩子们要去读书认字。
听到这个消息,人们没有太多的动静,不过也没人反对。
“大人也要去。”
“傍晚的时候,趁着还能看得见,要去读书认字。”
管事话音刚落。
众人就不满了。
累死人了,是不想倒头就睡,没那功夫。
“去不要去看自个,不强求啊。”
管事声音大了起来。
庄子里的管事都很凶。
不凶的人当不了管事,庄民们的声音被压了下去,管事凶狠的说道:“你们以为庄子里办社学容易啊,想让你们多读书认得字,还不是为了你们好,愿意领情的,不愿意领情的,也别抱怨。”
如此,众人才没有了言语。
“你也去。”
汉子对儿子说道。
“我不去。”
后生不同意。
汉子瞪了一眼。
后生不敢再回嘴。
“要去社学认字的来找我登记,社学那边好统一安排。”管事交代了后,就让众人解散。
来报名的人不多。
后生在父亲的眼神下来到管事身边。
管事身边只有几个人。
“马林,就你去,你老汉不去啊。”管事热情说道。
哪些人不错。
哪些人不能给好脸。
管事心里头门清。
马家父子做事勤勉,性子憨厚,非常好的一家人,所以管事对他们两父子也不错。
“俺爹不去,俺爹让俺去。”
“你爹是对的。”
管事笑道。
“少爷让你们读书,这般浪费精力的事,对少爷又没有好处,总不是希望培养你们。”
“认得字,会算数,才能有机会,以后为少爷办事,总不能一直没出息吧。”
管事向几人说道。
马林连连点头。
如果以后能不种地,那倒是不错。
种地太苦了。
没人想要种地。
如果自己也能当管事就好了。
马林眼神羡慕。
社学是一间普通的民房。
各处送来的桌椅。
几个孩子围着一张桌子。
孩子们白天读书。
马林他们傍晚来读书。
马林这帮人,庄子里减少了一点活计,以免他们承受不住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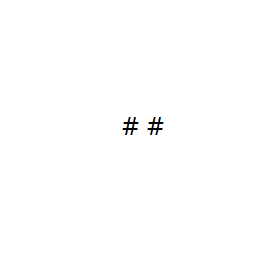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